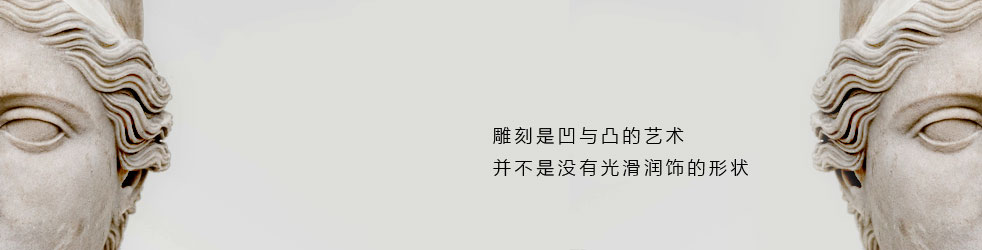
记忆中,小时候爱玩泥巴。
我的父母都是文艺工作者。父亲是一名优秀的二胡演奏家,音乐家。他自己创作的二胡独奏曲曾经在全国民族器乐比赛获奖,是一首描写天山美景的曲子,很有味道。曲名取得也很棒,叫《天山素描》。除了二胡,他还会摆弄萨克斯、单簧管等的很多种乐器。母亲是一名优秀的儿童话剧演员,得过的奖很多,但我佩服她的是能歌善舞,会弹钢琴,自弹自唱总是很精彩。母亲从不发脾气,总是微笑着。但是她很忙,不停地演出。曾经一年里只有三个月是在家里度过的,其余时间就在全国各地演出。据说小时候,有一次她演出几个月回来,我都不认识她了,在公共汽车上,突然想起她是谁了才一个劲儿的亲她,车上其他人都很诧异,母亲跟他们说明了情况,他们都觉得我很可爱。所以我童年的记忆多半是跟爸爸有关,记忆中他除了上班都会用心的为我做饭,在灶台边花上很多的时间。但他闲暇里绝大部分的时间还是把自己关在我家小小的卧室里跟他的乐器度过的,此外的大部分时间就是要为了维持生计而四处演奏赚钱。记忆中母亲后来异地的演出似乎也没有小时候那么多,她的闲暇也就都奉献给了为生计而演奏。有时父母亲会在同一地点,以一个乐队的形式出现。偶尔我也会跟着,乐队里还有其他有才华的叔叔阿姨,都能歌善舞诙谐幽默。演出多半是在别人的假期里才被需要,所以经常会是周末,于是我才有机会跟着他们。可惜我什么也不会干,就只是跟着,帮不上什么忙。
周末演出的早晨要起得比平时上班还早,这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毕竟那时我还小,无论周末与否,被窝里才是最爱的地方。但是,同样也因为我还小,一切事物对于我都很新鲜,所以那时父母们为生计而不得不从事的辛苦工作在我眼中却充满了乐趣:三五好友一起玩玩音乐,玩得尽兴,人家就会付钱,还有一顿免费附赠的丰盛大餐。我的任务除了跟到地方,每次随便遇到几个陌生的小朋友一起胡乱打发打发时间之外,就只有那顿丰盛的大餐!耶!可这一切从成人的角度看起来完全不一样,父亲觉得搞音乐挺辛苦。
是的,其实回头想想,我那时虽小,却也能体会出父亲的苦。
印象中渐渐清晰的又是父亲练琴的景象,一个人,形单影只。母亲在外地演出,我悄悄溜出家门去跟小伙伴儿撒野了。那时的夏天没有电扇空调,热!家里常常敞开着大门。我跟小伙伴玩野了时常是三过家门而不入,虽然不入,却能把屋里的情况瞟个清清楚楚,那一瞟有点像是按了相机的快门一样---咔嚓,也没时间仔细看,但真就是像拍了快照一样,那么的清晰而又印象深刻:父亲躺在厨房的地板上睡着了,就躺在地板上。现在想起这番景象觉得好心酸,当时自己怎么就没停下来叫醒他让他上床再接着睡呢?就那么没心没肺的白驹过隙了。
耳濡目染中,这些还都只是表面的“苦”,那些不表面的我当时看了却也看不懂吧。我不懂,但父亲懂得啊。
于是,父亲平时都是尽量回避音乐方面对我的熏陶。当我心头为某样乐器所动了,他总要当头棒喝,毫不姑息。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既因为对乐器的喜好,又带着对电视剧里大侠的崇敬,我悄悄给自己买了一只竹笛。带回家正准备好好稀罕稀罕的时候,遇上正要如厕的父亲,只得到一句,两个字“退了!”
看来我也真是与竹笛无缘,退了,从此不敢轻动念头。
后来我了解到,父亲的反应其实是因为早在心中替我拟定了人生方向—美术。
美术?
美术是什么?
他想让我将来搞雕塑。
雕塑又是什么?
我当时小学还是幼儿园现在不记得了,只记得自己不知道“雕塑”是什么,却挺因为听说自己将要成为雕塑家而沾沾自喜。
我不知道,但家里的大人们全知道。那时,“雕塑”对我而言就是玩橡皮泥,“雕塑家”大概就是祖父和父亲,因为祖父跟父亲都能够轻易地用橡皮泥做出十分像样的“拖拉机”:揉四个圆面饼,两个大两个小,再揉几个小方块儿,拼几下,用火柴棍一串,成了。一个巨棒的“拖拉机”,我超喜欢。他们比我做的好,我就拿着他们捏成的玩儿。我捏不成他们那样规矩的形状,用今天的话说--我属于“创作型人才”,总是胡乱捏些小玩意儿。
时间久了,橡皮泥被一遍又一遍的捏来捏去,从原来的五颜六色变成了灰色,我的手艺也跟着有了长进。我开始捏十二属,“子鼠、丑牛、寅虎……巳蛇”,这“巳蛇”可真是难住了我。我跑去问姨奶。她接过橡皮泥双手搓了几搓,一个长长的泥条子出现了,接着她把泥条子盘啊盘,盘成一个小圆盘,留着个头立着,在上面点了两个点儿。嘿,一条“巳蛇”就这样出现了,原来姨奶这么厉害!家里的雕塑家可真多。这以后,我做十二属,“巳蛇”都按这个法子做。直到今天,姨奶还是逢人就讲她当年教我捏蛇的故事,不知听了多少遍。以至于我现在都搞不清是自己当年就清清楚楚的记住了这件事,还是后来听她讲得多了,再也难以忘怀。
后来,我做出了我的“十二属”。有那么一个阶段,这几乎成了我的招牌。只要家里来了客人我就会被唤至一旁,展示我的“高超雕艺”,不知道有多少回。据祖父说那时我的“雕艺”也是出神入化,当年上幼儿园的时候,老师一早是要把小朋友从家带来的所有玩具之类的东西全部“收缴”的,直到放学的时候才会尽数归还。这是当时人人遵守的规定。但是,我当时每天都带着橡皮泥,却从来没上缴过。祖父说我那时都是把橡皮泥藏在裤兜子里轻松过关的,他管那叫“卡巴裆”。每次到了放学他去接我的时候我总能交给他全套的“十二属”之类的,所以他现在还常说,“我孙子当年的雕塑都是从‘卡巴裆’里做出来的”。我挺爱听他讲我这段光辉岁月的,但是,想想也不对呀,真在“卡巴裆”里做雕塑,那多难呀!
后来上了小学,“十二属”就做的没有那么勤了。不是因为学习忙,而是因为兴趣发生了变化手里的泥巴也就跟着有了变化。那时爱看动画片,边看边捏,《小飞龙》、《变形金刚》什么的。家里的大鱼缸能有一米多长一米多高,最上面盖着玻璃板,玻璃板上面就成了我展示作品的平台。就连工程部队组合的大力神都捏出来了,更别说擎天柱威震天了。就连颜色都是用了跟原著里一样颜色的橡皮泥对号入座的,在我印象中真叫一个棒!
那会儿在学校,大家都是男生女生搭配着做同桌。忘了是什么原因,我曾经有那么一个阶段是跟两个女同学一起,三个人同桌。我坐中间,上课的时候开小差儿,表面上故作镇定,两只手就藏在书桌洞儿里玩泥巴。做个小飞船,翅膀里面剪一小段铁丝,降落之后还能把“机翼”收拢。我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怕被老师发现,俘虏了我的“飞船战队”去充公。谁知道跟我同坐的两个女同学真是大胆,其中一个见老师转身写板书的空当儿,抓了我的飞船就作起飞状,我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就从书桌洞儿“飞”了出来,直“飞”到大家视线的高度,飞向坐在我另一边的女同学。另一边的女同学见状极其配合的接过来又飞回了书桌洞儿,并完成了降落。整个过程真是让我惊心动魄,好在写板书的老师错过了整个“空军表演”的过程。
那时课不多,学校时常要装修。我们被安排在去附近的学校借教室上课,这样一来常常只有半天课,下午通常都是自由活动的时光。我父母都很忙,所以我的大部分闲暇时光都被安排在祖父家度过。那个时候电视还不是什么不新鲜的玩意儿,所以经常是全家老小围坐观摩的。大人们显然觉得我做个快乐的小孩儿就行了,并没打算要求我学习如何优异。所以我经常可以很自由的选择打打游戏机,到户外跟小朋友捉捉虫,或者看看电视什么的。我当然没有什么自制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会没事的时候自己想想,我要做个好孩子,所以应该做作业,不应该总是玩儿,绝对不会。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的自己做什么都好,对今天总是有益的。当他们围坐电视机前,我就拿着橡皮泥凑过去,看见里边演什么就捏什么。有一次,二舅姥爷来做客,我又被唤至一旁进行表演。那会儿特别热衷于捏大狼狗,可能是那一阵子电视里总有警犬义犬之类的电影吧。大狼狗捏罢,二舅姥爷自然是一番夸赞。想想成年人对他们眼中的小小毛孩儿要求能有多高呢。我记得他十分惊讶的说:“这么小的孩子就能把这后腿的解剖结构都拿捏得这么到位呢!”记得当时在场的大人们都很开心,我自然是最得意的那个。但是,“解剖结构?”拜托,我那时哪里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只不过人家表扬你,还表扬的那么真诚,你都不好意思不认的。不过我那时的大狼狗真的捏的惟妙惟肖的。
后来上了中学,学习的压力一下就变得大的不行。我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个猛子就扎进了各路的“题海”,“卡巴裆”里再没有了橡皮泥。即使是后来考上了中央美院附中,每天都在学习真正的美术了,甚至后来上了中央美院真的选择了雕塑专业,始终都没能让我再重温当年玩儿泥巴的乐趣。
直到今天,当我把这些文字敲进电脑的过程中,我才又遇见了当年那个怀揣着橡皮泥的小毛孩。时隔多年,我想说“久违了,小朋友!久违了,快乐!”
2015-4-23
发表评论
请登录